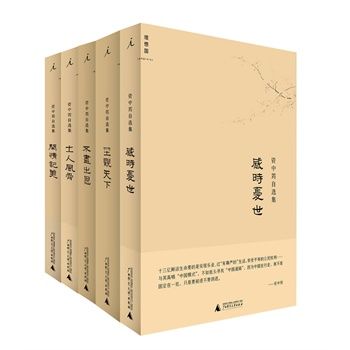 《不尽之思》
《不尽之思》记者: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这在大部分知识群体中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在大的共识下,实际上隐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中有一些始终以自己的真诚和良知守护精神家园,也有小部分还没能根本上从旧思维中转换过来,更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诚实,他们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其表达更多服从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没有身体力行,又谈何肩负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而言之,启蒙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该怎样进行启蒙等问题,我觉得还有必要做出进一步阐述。
资中筠:关于启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
记者:您说到了群众性的启蒙。实际上,启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众的启蒙。和城市化进程中民间社会团体衰落、解体有关,当下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普遍是脱离大众的。相比而言,在民国时期,乃至封建社会,通常有较高文化涵养的开明乡绅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府与民间交往的“介质”,客观上起到文化开蒙和引导的作用。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乡村日益衰颓,留守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年人进城当了农民工以后,未必能经常接触网络等新媒体。即使有所接触,也可能找不到适当的途径去领受新的思想冲击,电视也许是一种途径,但无关思想启蒙。所以,对启蒙如何面向大众这个问题,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说过的,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是否包含了这样的思考?
资中筠: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记者:现在被视为启蒙“先锋”的,是一些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追随者众,备受推崇。但在我感觉里,诸如“意见”是怎样被代表的?“领袖”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并不清晰。而且,此称谓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观点的天然正当性,但其中是否已经预设了独立、自由的价值立场,是大有可疑的。您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当下且不论面对政治时,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独立,即使是涉及到习见的学术论争,也难见超越团体、社群的客观冷静的评析。
资中筠: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在目前这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记者: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等,是当下面临的颇为棘手的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有人甚至发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
资中筠:在一个诚实守信处处碰壁而坑蒙拐骗风险很小的制度下,道德滑坡是难以避免的。
记者: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识界人士,认为要建立核心价值观。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所指为何,及如何真正达成等问题上有争论有分歧,难以形成共识。
资中筠: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的,这就是普适性的价值观。它存在于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公认的善恶标准之中。如果不带偏见的话,把每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抽出来,包括儒学的精华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同多于异。越进入现代,人类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无论走到哪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善、恶,好人、坏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国界民族而异,否则为什么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把监狱(剥夺自由)作为惩罚?那么,没有法律根据,无端侵犯或剥夺别人自由就是恶行。所以最高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适的。
记者:的确如此。您说到的是非、善恶,包括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我想都因其有普世性被普遍认同、接受。但具体到特定的国家、民族,一般领导层都强调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因此,普世的观念在施行过程中会有很大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约性,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称,“文化无国界”。您怎么理解?
资中筠:第二层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当然有些陋习、恶俗是应该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样。每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自己的表现特色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不可能从上而下强行设计出一套来让大家认同。
记者:我想这方面很难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所以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资源。长期占据我国思想正统的儒家文化,正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以您的观察,从中能否提炼出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又该是怎样体现的?
资中筠:如果要发扬儒家的精神,那么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导道德价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则”,然后感化民众(小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沦于伪善。
记者:从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拿来做此类比。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五四”倡导的启蒙精神,很快就在救亡的时代命题下失落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起初在政治的影响下,也产生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之后很快就被边缘化。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主流层面,甚至于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学的影响。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记者:但知识分子未必甘于这种边缘地位,他们向往五四时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迸发出来的活力和激情。近读几位学界中人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些话题,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一些学者讨论过,而且相比讨论更为深入。这感慨声中,有欣慰也有颇多无奈。
资中筠:“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我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是后来的革命压倒了启蒙。
记者:怎么理解,能否展开谈谈?
资中筠:我认为启蒙原来是与救亡一致的,而且启蒙就是为了救亡。从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才开始向外寻求强国之道。由枪炮到声光化电到政治制度到立宪,然后发现“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严复语)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的建设并没有中断。后来是由于以一种思想指导革命,再次“定于一尊”罢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于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个人解释,所有的人,包括硕学大儒,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或者干脆丧失了这个能力,这才彻底压倒了启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机。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与思想解放同时进行的。也就是重新启蒙。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记者:您一直关注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并为此忧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次会议上称,北大等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他这么说未必是危言耸听,利己主义的思想泛滥,会侵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根基,更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公民社会。
资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钱理群教授对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忧思。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青年人太多实用主义,太少理想主义的问题。当然钱老师在大学多年,体会更深。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意气风发,求知欲旺盛,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可望继承五四传统。北大尤其是重镇。可惜这种精神被扼杀了。九十年代经济起飞而人文环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缩。关于现行教育制度,批评的意见已经很多,我不想多说了。总之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各个方面把青年学子引向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精明、实用的取向。我有时也有点同情当代的学生。
还有留学生。过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诚意要用所学的知识改造中国。现在多数留学生到国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可厚非。有人还愿意回来作些贡献,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海归”不满意在国外的地位,回来谋求个人的发展,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前进,而且有意投权势之所好,与潜规则同流合污。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话语权,比钱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种中国大学生可能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还要严重。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您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意识的专家、学者。读您的文章,每每为您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折服。您不单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做到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在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关系的思考上,也同样如此。我想,这大概得益于您早年从事的外事工作,还有近年国外的游历生活。事实上,您也曾提到,我们应该把思维从“前全球化时代”,真正转向全球化时代。
资中筠:我看问题常常超越国界,从全球看,从大历史看。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问题有关,但是也与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民国元年(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那部教科书贯彻的宗旨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不但讲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颇具世界眼光,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并且强调人类的博爱。我本人没有赶上学那一套教科书,因为那还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
再加上我上面说的,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就是民族危亡之秋,所以习惯思考超越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较少关注和追求物质享受。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太实际、太实用,对社会、对世界、对暂时与个人利害无关的身外之事缺少好奇心,当然这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把人变成考试机器也有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有关。但是毕竟,未来社会是需要青年去创造、去革新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尽可能的视野开阔一些、目光放远一些,对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对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
记者:和许多从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您也经历了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心路历程。您最后激流勇退,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我想一定有像贝多芬之所以用生命谱写乐曲那样“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支撑着您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追问和探索?
资中筠: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雄心,只能说是惯性作用和本能推动我去写,欲罢不能。我还有一定的精力,不读、不写,那整天呆着做什么呢?有些是被动的。例如现在是接受你的要求,在你的推动下,说了这么多话。当然,既然我认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也愿意有机会与更多的人分享。与人交流也是我的兴趣之一。特别是如我一再说过的,无论如何,希望在中、青年。所以我的作品多一些青年读者,我的话得到青年学生的倾听,我会感到欣慰。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