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憨夫子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何”字在空中停顿了足足三秒,憨夫子微闭双目,手舞足蹈。他的吟咏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我从梦中惊醒。
憨夫子姓何。不过南巷的街坊,似乎都忘了他的尊姓。自打我记事,所见诸人,不是称他“憨老师”或“憨夫子”(他喜欢咬文嚼字,满口之乎者也,这种人,吾县以夫子视之),便直接呼他“老憨”。我原以为,“憨”是“何”的变音,父亲则说,老憨生具异象,双眼白多黑少,五岁才会叫爸妈,人家孩子流口水,那是看见了鱼肉,他流口水,那是看见了书,因此他从小就被街坊称作“老憨”,叫了这么多年,谁还记得他姓什么呢。
憨夫子的事迹,滋养了我们贫乏的童年,熟识他的人,都能说道一二。而且这些事迹,都与他的憨有关。譬如他一边烧锅,一边看书,不仅把饭烧糊了,还将自己的布鞋当柴禾塞进了熊熊火中;他给女儿喂红薯稀饭,喂到一半,诗兴大发,便去挥毫泼墨,待诗写好了,回头一看,那半碗红薯,却落入了邻家的狗嘴里,自此女儿再也不让他喂饭。
这些都是寻常事——其实认真说起来,憨夫子绝非什么异人。他的生平,清白如吾乡的手磨豆腐:贫家出身,师范毕业,中学教书,娶妻生女,与世浮沉。他所异于常人之处,一是爱书成痴,二是爱诗成魔。不想这吟风弄月的嗜好,最终殃及他的教师生涯。他教了十五年高中,因爱在课上谈诗词曲赋,为家长所检举,称其不务正业,耽误了学生高考,缘此罪名,被学校从高中部贬到初中部。然而他不知改悔,仍旧给一脸懵懂的初中生讲格律,谈平仄,校长闻后大怒,遂禁止他登台授课,发配到阅览室看门。这在吾县的教育界,同样是一桩谈资。
父亲与憨夫子自小相识,曾有意请他为我发蒙,为奶奶所阻止,说怕传染了他的憨。后来父亲拿我的作文请他指正,他大喜,送了我一本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我读高中,恰巧是他在高中部的最后时光。他实在不太擅长讲课:一口乡谈,笨拙至极;自说自话,丝毫不顾学生的感受。他最得意讲古诗文,讲廉颇蔺相如列传,便抱上一摞《史记》;讲杜甫诗歌,便高举《杜诗镜铨》……他在台上顾盼自雄,台下一片窃窃私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他的叹息穿越了那仓皇的三年。
上大学之前,我去他家辞行。时值炎夏,他正伏案读书,奔腾的热浪使他破落的书房愈发逼仄。他老了,瘦骨嶙峋,脖子漫长——后来我读余光中写一个人的瘦,“瘦得像耶稣的胡须”,眼前便浮现黑而瘦的他。他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二人坐定,却相对无言。临别之际,他钞了一首旧词送我,记得最后两句是:方正做人勤笔墨,切莫为官。
2013年6月
王老师
王老师有一个极文雅的名字,叫王敏之,他家的小院,叫莲宅,他的书房,叫守缺室。单是这些细节,便注定了他在南巷的孤独。
王老师不是南巷人。我七岁那年夏天,他从曹乡调到县中学教书,看中了南巷的幽幽古意——他说以吾县之大,惟有南巷,还残存一丝文气——便在此置房。搬家之时,惊动了半条街,街坊纷纷说:开眼了,见到了活着的孔夫子。原来王老师搬家,动用了两辆拖拉机,前一辆装满了家什,后一辆装满了书。他在乡下,如何藏书千卷,至今仍是一个谜。
半年后,南巷的街坊再度感慨:开眼了。王老师的穿戴,不分天气,永远是黑西装、白衬衫,头发与皮鞋一尘不染。与人说话,无论大人小孩,他都毕恭毕敬,诚心正意。傍晚,二胡的咿呀越过他家爬满青藤的院墙,盘旋于南巷的市井之上。街坊纷纷感叹:和乡下来的王老师相比,我们才是乡下人。
三伯是教师出身,会拉胡琴,且与王老师有旧。他在我家喝酒,听见王老师的二胡声,搁下酒盅,叹道:太哀了,人生不该如此。然后满斟一杯,一饮而尽。
因三伯的关系,我在听王老师授课之前,便去过他家。那时我好像刚上初中,颇能写两笔作文。王老师引我进书房,四面墙上挂满了字画,我指其中一幅行书念道:最可惜一片江山,更能消几番风雨。他笑道:念反了。我面红耳赤,问他这两句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人集古人的联语,上联出自辛稼轩,下联出自姜白石。“家国之悲,你还不懂”,他顿了一下,“最好永远都不要懂……”轻轻摇头,仿佛听见了窗外雨打芭蕉的寂寞。
初二初三,他教了我们两年地理。他上课,从来不拿教材,仅凭两张地图,便能讲大半学期,横谈表里山河,纵议古今史事,他硬生生将地理课讲成了历史课。这般不拘一格,怎么应付考试?王老师却有一大特长:押题。所以他带的班,中考成绩总是不差,他在学校的境遇,便不像憨夫子那样潦倒。
1998年,洪水来袭,吾县沦为泽国,曹乡受灾尤为严重。比灾难更可怕的是,救灾款下发至乡政府,如羊入虎口,最后落到老百姓手上,惟余一堆被吸空榨干的骨头。灾民忍无可忍,只能去县里告状,这状纸,便是王老师的手笔——这等事,只要乡亲开口,依王老师的性格,无有不允。
有一天,二胡的咿呀从南巷消失了。街坊窃窃私语:王老师进去了!
随后,发生了一件铁定不会载入县志,只可能在民间经久流传的奇闻:数百名曹乡的灾民,开拖拉机、三轮车,撞倒了县政府的铁门。然而民气浩荡的代价,却是坐实了王老师等领头人的罪名。
王老师被判七年。他服刑不久,莲宅易手。
2004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家,去看三伯,晚上在他家喝酒,不知何故说起了王老师,三伯说:死了,癌症,就是这个春天,保外就医,好歹死在了外面。说罢,他满斟一杯,一饮而尽。
2013年6月

丁老师
丁老师是我高三的英语老师,不过我在高二就与他熟识了。他到姨夫家里下棋,恰逢我在场,姨夫便让我先陪前辈杀两盘。第一盘,我祭出最拿手的邪门开局,八十回合,一败涂地;第二盘,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支撑到两百回合,战况惨烈,双方車马皆亡,丁老师用卒子逼宫将军,我再败。见我垂头丧气,姨夫安慰道,在吾县,能赢丁老的人,或者已经死了,或者尚未出世。丁老师连连摆手:“别吹了,让孩子笑话!”
丁老师与姨夫都是吾县知名的象棋高手,二人风格不同:只要见人下棋,姨夫都要往前凑,不管是在公园,还是在医院(姥爷生病住院,他去探视,转眼便不见人影,最后表哥在输液室找到了他,他正与一个病人下棋!);丁老师则是讲究人,对环境和对手都十分挑剔。姨夫说,丁老极少和庸手下棋,你能陪他下两盘,幸何如之。
丁老师年长姨夫十岁,姨夫一直敬称他“丁老”。等我上高三,台上的他已经年过六十,精神却胜少年,满头黑发,如怒放的钢针,直指苍天,方脸威严,皱纹似刀刻,身板粗壮,如一面不屈的盾牌。学生都说,丁老师一点都不像教师,而像饱经风霜的退休工人。
季羡林先生帮北大新生看行李的故事,近乎传说,丁老师被误作门卫,帮学生抬行李,正发生在我们身边。高一新生入学,满载而来,在校门口撞见丁老师,喊道:“门卫师傅,能不能搭把手,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丁老师二话不说,背起一大包就走。两年后,谜底才浮出水面。高三开学,第一堂英语课,丁老师大步走上讲台,我的同桌何启腾地站起来:“这老头不是门卫么?”
老实说,丁老师的英语课,并不太受学生欢迎。他一口皖北土话,“国”读成“guai”,“阴谋”听来像“阴毛”,常引学生哄笑。普通话不佳,自然影响英语发音,最终殃及我们的口语和听力,遂有促狭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三寸丁”,暗讽他的身材。
我将此节当作笑谈,说与姨夫听,他脸色微沉,说你们真不懂事,丁老一大把年纪,退休返聘,给你们上课,你们还挑三拣四。打开了话匣子,他谈起丁老师的凄惨身世。文革期间,丁老师被判刑劳改,精通英语竟成一大罪证,他在外服刑,唯一的孩子乏人照管,染病身亡,其妻经此变故,患上了精神病,未等丁老师出狱便撒手人寰,丁老师自此心灰意冷,孤身至今,一腔心血,尽付学生。
姨夫说,有一年除夕,他到丁老师家里,请其过去吃年夜饭,丁老师孤身一人,正在打棋谱,楚河汉界一侧,冷酒一杯,残存的花生米如孤独的石头。姨夫满心酸楚,竟不知如何开口。丁老师终未去他家过年,理由是,去了,回来更寂寞。
姨夫叮嘱我,有空可与丁老聊聊,他太寂寞了。然而在丁老师面前,我总有些莫名的畏惧,不知这一压力,是来自他那张方正的脸孔,还是他所承受的苦难。对我而言,他就是历史。
我对丁老师唯一的报答,当是高考那年,我的英语成绩,全县第一。这是吾校从未有过的殊荣,丁老师更是喜不自胜,一定要请我喝酒。我无限惶恐,终究还是婉拒了,低头与他道别,我不敢看他写满历史的脸。
2007年,丁老师正在讲课,突发脑溢血,死在了讲台。死得其所。
姨夫帮忙操办了后事,在他坟前,烧掉了一副檀木象棋、三本棋谱。
2013年7月
古老师
古老师教了我三年政治课。在我们学校,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没有之一。如你所知,教高中政治,历来是一项苦差事,没头脑的老师教不好,有头脑的老师更教不好。古老师自然有头脑,而且是我们学校甚至我们县教育界最杰出的头脑,据说他琢磨了好多年,头发掉了几百根,才悟出破解之道:让上课归上课,考试归考试。
古老师上政治课,从不照本宣科,他连教材都懒得拿,将保温杯往桌上重重一顿,如惊堂木响,便开始说书。一堂课,起码有半堂题外话,从白起讲到白蛇,从鬼谷子讲到他撞鬼的故事……何启说,听古老屁讲课,就像听单田芳讲评书。我们大呼同感。
“古老屁”是古老师的外号。在吾县,屁不仅指一种气体,还可以作为动词,其意同“说”。譬如说“他这个人真能屁”,意思是这厮能说会道,当然,一用“屁”字,便有贬义之嫌,暗指胡说八道。
然而古老师并不以“古老屁”为耻,一贯唐突的何启,路上遇到他,喊他“古老屁”,他还含笑应答。他对自己的辩才十分自得,号称能把死人说活,能把活人说死。他常叹教书屈才,虎落平阳,单凭他这张嘴,应该当外交部长,周游世界,舌战列强。后来我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讲话,暗想,他们的口才还不及古老师一根毫毛。
上课讲白话,考试怎么办?古老师对我们打包票,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暗地研究高考政治试卷,已经摸清了命题规律,来年考什么,尽在老夫掌握之中,尔等不用担心。台下掌声雷动。
古老师虽是学生心里的神,在其同事口中,名声却不佳。他为人圆滑,擅长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最能讨校领导欢心。曾与他同一办公室的憨夫子,直斥他“人品可鄙”。“古老屁”之外,他还有一个外号,叫“泥鳅”,暗讽他滑头,从不得罪人。
有时古老师觉得委屈,便在课上向我们诉苦,讲述他三起三落的苦难史。青年时期,他被打成右派,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他因直言贾祸,被撸去教委秘书的职务,发配到我们学校当老师。往事不堪回首,他摇了摇比常人大一号的脑袋,意态萧索。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四顾茫然。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古老师玩世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苦闷与坚守。他好酒,晚自习课上,偶尔面颊酡红,一身酒气。王绩的两句诗,常挂他嘴边:“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他教了十来年高中政治,竟不是党员。校长劝他写入党申请书,他悍然答道:别污了我的纸笔!正因此,他和领导关系再好,却不得提拔。
古老师常说,人生两大美事,睡回笼觉,娶二房妻,他都实现了。他的第二任夫人,不仅貌美如花,且能患难与共。四十岁那年,古老师得一子,名古麓,绰号“咕噜”,大脑袋酷肖其父。
我与咕噜同龄、同级而邻班。高考之时,这小子运气好,恰巧坐我前排,考数学那天,他两次回头捡橡皮,抄了我特意放在桌角的十道选择题,净得五十分,助他考上了他心仪的师范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咕噜在望月楼摆酒,请我和肖辉等人。古老师亲自作陪,开了一箱十年陈的剑南春。他虽自命酒徒,然而毕竟年近六十,敌不过我们这些青壮的后生,中途便醉倒。最后我们搀扶他回家,一路月华,一路踉跄,快到学校,他酒醒了,仰望满天星斗,忽然高声吟道: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2013年7月
(节选自羽戈《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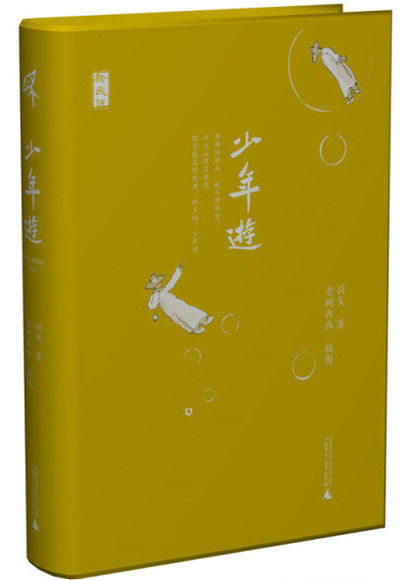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